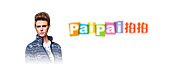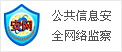□羊城晚报特约记者 马国川
法国大革命只搞了一次,之后法国没有再暴力革命过;克伦威尔死后,英国不再革命;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再也没有暴力革命……有一次革命就够了,下面应该考虑如何修正、协调、妥协,这比革命要上算。
许倬云
历史学家。江苏无锡人,1930年7月生,求学于台湾和美国,1962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先后执教于台湾、美国和香港多所知名大学,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学贯中西,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研究领域主要在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代表著作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等。
为什么改革跑不过革命
羊城晚报:有学者说,清末形成了“改革和革命赛跑”的局面:一方面革命党人鼓动革命,一方面清王朝实行废科举、改官制、设咨议局等改革措施,史称“晚清新政”。那么,为什么改革跑不过革命呢?
许倬云:“晚清新政”并不意味着慈禧太后真的要搞改革,而是迫于当时的形势,不得已而为之。慈禧是一个有手腕有权谋的女人,但是没有见识,热衷权力。“晚清新政”的改革成果很有限。
辛亥革命前夕,中国本身固然处在改革和革命之间,看上去似乎有选择,实际上中国的选择余地并不多。因为当时维新的力量并不大,维新力量在戊戌政变时遭到了重创,守旧力量重新抬头,城市里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多少。所以,整体讲起来清末改革没有多少准备工作,无法取得实质进展。例如,虽然各省成立咨议局等民意机构,但基本上都是空的。
羊城晚报:为什么革命力量会在广东开始壮大起来了?
许倬云:等到袁世凯称帝的时候,孙中山就往广东走,一些人也跟着往广东走,虽然广东是一个小小地方,没有多少力量,但是真正是全国希望之所寄。孙中山在广东局促一隅,却终于得到了两个意外帮助。
第一拨意外的帮助,就是许多沿海地区的留学生,纷纷往广东聚集。一批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帮孙中山做许多事,包括帮助他完成他的理论建构,帮助整理财政,等等。另外一拨意外的力量,就是苏联革命以后,孙中山实行“联俄容共”,使他得到了左边的助力,有了组织工作,也使他得到了武装力量。
羊城晚报:文武两拨力量终于使得广东这个革命基地成为气侯。
许倬云:对,中间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1914年欧战开始,在华的欧美实业,包括商业工厂都纷纷撤资回国,上海、天津、武汉、广东等四个地区的民族工商业借机在夹缝里发展起来。再有,在这个时候大批欧美回国的留学生参加了许多欧美人士在中国设立的学堂,将其转化为中国的教育机构。沿海城市出现不少报纸杂志。中国都市里发展的中层阶级、民间资金和知识分子、知识传播都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中国的城市地区,民智渐开,中国得以逐渐走向现代化。
邓小平的政策
与北伐后南京政府相当类似
羊城晚报:抗战结束之时,蒋介石声望如日中天,中国也跻身战胜国之一,可是不数年国民党政权就土崩瓦解,这是非常令人费解的历史结局。
许倬云:国民党八年抗战精疲力尽,城市基地几乎全部丧失。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政治、经济和军事诸项决策中十有九错。例如,全国希望政府能够和平建国,能够实践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民主宪政,然而蒋介石以“反共”为号召更加强了集权统治,知识分子推动民主化遭到迫害,学生运动更遭武力压制,因此人心丧失。最后一根压死骆驼的稻草是“金圆券”的币制改革,一年不到,金圆券已成废纸,全国中产阶级为此破产。国民政府的心脏地区民心大失,前线作战部队士气不振。于是,国民党败下阵来,共产党取得大陆的统治权。
羊城晚报:黄仁宇先生曾说过,国民政府重组了中国的上层结构,中共则整合了以农村为主的下层结构。
许倬云:对,在大陆毛泽东继续走农村路线,以党的组织力量动员农村。因此中共在1949年以后能够编组中国广大的农村,撑起以农民为基础的国家力量。黄仁宇认为,中共改造了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政府力量从此可以下达农村。这一改变,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从“大跃进”到“十年动乱”,使得本来可以建设的阶段完全浪费。最终轮到邓小平,才改革开放。邓小平改革开放采取的政策和北伐以后南京政府的政策相当类似。
羊城晚报:邓的经济政策和南京政府的经济政策是相似的吗?
许倬云:都是经济市场化,但是也有一个大的差别。毛泽东30年的组织努力,留了一个遗产,就是大陆上有许多小集体出现。城市里有“单位”,乡镇也有小集体,它把散乱的农村力量集中成一个过去没有的集体力量。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这些集体力量就变成单位企业、乡镇企业的本钱。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乡镇企业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不是仅仅依赖外资。
“南京十年”经验在台湾翻版
蒋介石到台湾时,台湾已经相当程度城市化,大陆过来的大批城市知识分子继续举办现代学校,学术界也得以继续发展。台湾发展浓缩了当年蒋介石没走完的路途,“南京十年”经验在台湾翻版,而且做得更彻底。当然,在此期间蒋介石也有一段白色恐怖时期。等到蒋经国执政,接下来也是改革开放。所以,蒋经国和邓小平两个人等于各走一枝,都走上了改革开放途径。
总起来说,孙中山出现以后中国走了革命的路线,继续不断在革命,蒋介石、毛泽东各自继承了孙中山的一部分。邓小平和蒋经国个别继承了毛蒋的一部分,可是钟摆转到比较靠中间的地方。这是延续性的“正反合”的过程,每一段都是“正反合”的过程。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前面都有没走完的过程。
所以,辛亥革命以来的一百年,中国颠颠簸簸,走得确实很辛苦。我个人理解,固然这中间有多次政府的转换,也有外部的侵犯(如八年抗战),整体来看,中国仍然在做连续工作。100年的路是“正反合”的过程,是辩证式的进展,中国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断革命论”很恐怖
羊城晚报:近两年大陆和海外一些人士正在热议的话题“中国模式”,您怎么看待广义的“中国模式”?
许倬云: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我们经不起冒险,不能100年或50年继续走一条路到底。我们把所有的鸡蛋摆在一个篮子里,摔一跤鸡蛋全都摔光了。如果把鸡蛋摆在多个篮子里,最多摔一个篮子。我这完全是从实用的观点来看“中国模式”。
羊城晚报:对大陆来说,“摔一跤鸡蛋全都摔光”的危险确实存在。
许倬云:有一次革命就够了,下面应该考虑如何修正、协调、妥协,这比革命要上算。
羊城晚报:辛亥革命以后,中国陷入长期的军阀混战,100年间有近一半时间处于内战状态,因此一些人士对辛亥革命提出强烈批评:如果当初不这样做,而是按着清末新政去做,也可能早就实行宪政了。据此,他们提出了“告别革命”的观点。
许倬云:对“告别革命”,我也有同感,因为我的岁数大,看见过内战的惨烈局面,“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我也听过十年动乱里,人的尊严如何被践踏,人性怎么被扭曲。中国经不起再来一次。
我们回头看,法国大革命惨不忍睹,雅各宾就是大陆十年动乱的微型啊。法国大革命只搞了一次,之后法国没有再暴力革命过。克伦威尔砍了英国人的头,克伦威尔曾经以护国主的身份专制独裁,他死后英国不再革命。得了一次经验就够了,不敢再做了。美国独立战争以后,华盛顿飘然下野。后来又有一次南北战争,此后美国再也没有暴力革命。
老实讲,辛亥革命损失不大,军阀混战损失就大了。尤其1945年到1949年的国共内战损失极大,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浩劫,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损失也极大。以暴易暴,用一个暴力换来另外一个暴力,没止没休的,所以我对“不断革命论”是极反感的。有一次辛亥革命就够了,不要再做了。
马国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