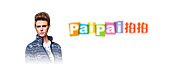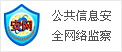核心提示:当林彪还在革命阵营的时候,我认为他政治上开朗,有军事指挥才能;同时也感到他有两个缺点“一是过分自尊,二是不大容人,性格上偏于沉默寡言,城府很深。”

本文摘自《萧克回忆录》 作者:萧克 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
衡宝战役的胜利,是中央军委的正确指导和四野各级指挥员的正确指挥以及广大指战员奋勇作战取得的。在讲这一胜利的时候,不能不说到林彪。
前些年,有人问我,衡宝战役林彪怎么写?我说:“应该实事求是地写。”当时,他是四野司令员、衡宝战役的指挥者。在战役中,抓住机会消灭白崇禧的主力,打得对,打得好,他注意抓白崇禧的弱点,以自己的优势兵力和指挥的灵活性,有力地打击敌人。他善于集中兵力,也谨慎,即便自己处于优势,也不轻敌,战术上总是以优势对劣势。从战术上集中兵力抓较孤立的敌人,与军委大包围的指示也没有多少矛盾,在大包围中可以采用战术包围,如果不注意大包围而专从战术上抓敌人就不好了。初到湖南时,他有这种倾向,经军委指出后没有看到他有不同意见。衡宝战役,是他指挥的,整个进军中南也如此。
但在这次进军中,我也看到了林彪的老毛病——过分自尊,仍没有改。
衡宝战役结束时,我情报机关掌握歼敌数目,有两个材料:一个是敌第7军全部加46军之38师,一个是第7军全部加38师1个团。当时尚未查清,林彪就向上报告,说歼敌第7军全部及38师。几天后发现敌38师仍在全县附近,但他不更正。我认为,林彪在战果未查明前,夸大战果以邀功;查明之后,又不改正以保面子,大不老实!
对于林彪,我比较了解。从井冈山起,我当连长、营长、纵队司令,他都是我的直接上级。我还先后两次当过他的参谋长,第一次是1929年,林任红4军1纵队司令,是年秋,我由他属下的第2支队长调任纵队参谋长;第二次就是这次进军中南,他是四野司令员,我又当了近一年的参谋长。有人说我到四野是林彪点名要的,我不清楚。有的说我后来调到北京,又是林彪把我挤走的,我也不清楚,反正都是军委的命令。我从入党以来,担任任何工作,都是党和行政安排,长期如此,形成一个观念,我是为党工作。从自己的性格来说,也不屑为个人驱策。
当林彪还在革命阵营的时候,我认为他政治上开朗,有军事指挥才能;同时也感到他有两个缺点“一是过分自尊,二是不大容人,性格上偏于沉默寡言,城府很深。”自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后,他以“紧跟”自居,有些人便认为他一贯正确。
在进军中南过程中,我和林彪合作是好的,他在工作上、业务上对我是信任的,但也有过一次争议。那是在1949年6月中旬,我们同到汉口。有一天,林彪同我谈中南地区的工作重心问题。他说中南地区几年之内应以农村工作为中心,并说了若干理由。我听了以后不以为然,因为中央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已经提出了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我也讲了些理由,但林彪听不进去。过几天,他便在中南局会议上通过了他的提法。7月1日,他又在武汉地区纪念党的28周年大会上大讲了一通。次日,《长江日报》就将他的讲话全文刊登了。听说当时他将这个意见报告了中央,中央表示可以按照自己所设计的几个步骤去布置城乡工作。
1950年2月,邓子恢从北京回来,在华中局传达中央意见,中央认为华中局去年夏天那个口号(即中南地区以农村为中心)与中央精神不衔接,要华中局自己讲一下,否则中央要讲话,因为“你们登了报”的。我在会上发言,中心是同意中央的意见,还讲了我的看法。但林彪在两天的讨论中含糊其辞,对中央的指示不置可否,却说我“否定一切”,从此产生嫌隙,耿耿于怀,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声望无端或夸大其辞,加以指责。1952年冬对改变全军军训计划的批评,1958年军队开展所谓的反教条主义,庐山会议后的所谓批“右倾”,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超乎常情地对我进行指责。
以他的当时的地位和影响,那种指责对我造成的危害是可想而知的。然而我始终认为自己对党、对人民是忠诚的,即便被无端指责,也泰然处之。当然,也无可奈何。
我同林彪共事多次,知道他的个人尊严很重。在革命游击战争时期,军队的民主作风好,同事问即便上下级也可以互相批评,可以争论。在当时对这种方式是无人非议的,林彪也如此。但他成为一方重寄后,名望大了,地位高了,自尊也更严重了。他把自己的缺点推向极端,就不习惯于过去那种党内生活了,但我还是用老习惯同他打交道,他不能容忍,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
解放以后,由于党的“左”倾错误,他从政治上的投机心理和个人野心出发,大搞个人崇拜,把领袖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从而扶摇直上,成为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利令智昏,直到仓皇出逃,暴死沙漠。想到他的过去,难免慨然;看到他的晚年,不禁发指。至于他为什么走到如此地步,人们可以从他的经历和思想意识,以及党内倾向和人际关系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