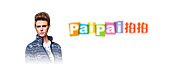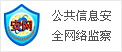郁达夫生前对鲁迅的评价意味深长,以为在文字上是有奇气的。鲁迅的思想,都是在与敌对的力量对比和抗衡的时候显示出来的。有趣的是他在阐述自己思想的时候,不是简单地布道,而是一直用形象的语言为之,显得很特别。我们注意到,在他和学者们争论理论问题时,表述方式却是诗化的,得庄子与尼采、普列汉诺夫的妙意,将复杂的问题形象化地表述出来,显示了一种高度。我们一些研究鲁迅的文章,不太注意鲁迅的表达方式,漠视鲁迅审美的特点和精神哲学的特点而谈论鲁迅,是很有问题的。
鲁迅认为汉语的表达应当有现实和诗意的情怀。写实其实是很难做到的一种精神劳作。在鲁迅看来,现实的复杂有时候不都是能用日常语言表达出来的。写实不意味着复写,而是要看到表象后的存在。除了批判理念、智性之光外,鲁迅一生对事物判断的那种诗意的表达,后人一直没能很好地继承下来。现代汉语越来越粗鄙,单意性代替了繁复性,文艺腔置换了诗意。其中的问题是丧失了汉语表达的维度,把语言仅当成工具,而非精神攀援的载体,不仅古意寥寥,连衔接域外艺术的冲动也失去了。我们和“五四”文人的距离,在表达的取向上就已经问题多多。
自然,每个时代有自己的语言方式,今人不应再返回过去。鲁迅的语言是不同于古人,也不同于同代人的。古代的语言在他看来是被士大夫气污染了。那些事功的书写和颂圣的文字,殊乏创意。而同代的语言则有江湖气和八股气,缺少的恰是生命的意志。那个意志不仅含有智慧,还有人性的暖意。我们现在却把那些幽夐的温润的文体放弃了。鲁迅跳出众多的表述空间,在寂寞里独辟蹊径,置身于时代又不属于时代,那就既有了当下意义,又有了纯粹的静观的伟岸。
鲁迅的表达很少重复,每一个话题都有特别的语境。他对生活的把握不是机械的描摹,而是着重复杂的不可理喻的存在。即使最愤怒的时候,也依然能将美丽的句式呈现出来。
在言说里,人们很容易进入精神的幻象。他的表达过程却一直避免进入这样的一种幻象里。旧的士大夫的一个问题就是常常自欺,而且欺人,人生的真相就被遮蔽了。新月社主张爱的文学,不满意左翼作家的理论。鲁迅就说,新月社不满意的是世界上还有不满意现状的人。这样的看法含着哲学的意味,实则是表达的悖谬的一种展示。作者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写道:“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一到了有钱,容易变成两种情形:一种是理想世界,替处同一境遇的人着想,便成为人道主义;一种是什么都是自己挣起来,从前的遭遇,使他觉得什么都是冷酷,便流为个人主义。”这样的语境,令人想起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的一句话:“对存在发问的时候,也必须对发问者进行发问。”鲁迅对言说的有限性的警觉,在提倡白话文的时候一直没有消失,他能够看出语言维度的开放性。
表达很容易落入俗套,这是他一直强调的看法。他用诗意的语言表达思想,其实就是颠覆这种尴尬。比如,讲思想与艺术之间的关系,他就说:“从喷泉里喷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在论述宣传和艺术的关系时,他说:“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然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是花一样。”这样的比喻很有跨度,也避免了理论阐释的单一性。他的杂文犹如这种笔法的同样很多。
语言也是一种幻象,而且是导致人进入悖论的载体。拆解这种怪圈,对语言的限制和反诘,对他是一种超越极限的快慰。鲁迅的语言造成了与背景隔离的效应,一方面进入市井,一方面不属于市井,于是存在的面孔便清晰了。他对中国社会的描摹,何曾是简单的图式呢?那种复杂里的凝视,存在着精神的伟力。旧式话语方式在此已失去力量。而他对新语境的营造,给我们以久远的感念。
鲁迅整理的古代文献有上百万字,翻译的作品有300万字。他对民间艺术的研究也很多。那结果是语言发生了变化,有疏朗自如之气,方巾味与腐儒味均无,倒是和古人相通者多。他谈到先秦两汉,讲起六朝、唐宋,都有灼见,说一些别人不说的话。有时候似乎也和古人为伍。比如,他曾说,现在的中国还仿佛是“明季”,都是读书阅世的一种心得。因为通晓古人之得失,方知今世之明暗。他的语言深处的古风,需暗自体味方可见到。
上世纪30年代的鲁迅,在翻译上给人很大的冲击。但那时候译界几乎没有人认可他的译风。他的译著因为生涩、直硬而受到非议。晚年所译之书几乎都无其杂感和小说那么流畅,仿佛有意与人捣乱。按当时的精神状态,他本可以写一些厚重之书,做自己心爱的事。一反常态的是,他却故意在文本上与思想上和旧有的习惯作对,文字趋于艰深,句子拗口,几乎处处可见反汉语的用意。梁实秋曾讽刺说是一种硬译。连瞿秋白这样的人,也不能完全了解其选择的深意。鲁迅在那时将自己置于译界的对立面。我看先生的一些短文,感慨于他对自己过分挑战的勇气。应当说,译苏联的文艺理论及小说,在他有多层用意,除了精神层面上的变革外,我以为重要的还有语言学上的思考。鲁迅觉得中国人的国民性出了问题,与思维方式大有关系。思维是靠语言进行的,问题是汉语的叙述方式存在着弊病。比如无逻辑性,没有科学化的范畴,概念不精确等等。在旧的语言中,大概只会产生诗化的散文,不会有科学理性的存在,至少没有数理逻辑一类的东西。晚年在着手介绍域外文艺时,他已不再满足于内容的传达,而着眼于表达的变化。不是从“信达雅”的方面考虑读者的阅读习惯,相反是逆着传统的秩序,原文照搬洋人的语式,使文句冗长、生涩,一些新奇难懂的句式不断出现。鲁迅相信,改造汉语不能不借用外来的语法,否则精神的表述永远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他甚至以为,汉语的历史就经历了外来文化的冲击。先秦的文章是一种模式,两汉魏晋大变,原因是汉译佛经激活了汉语,那一次冲击使汉语有了一次飞跃。后来汉语的发展又被封闭起来,不能自我更新。欲救死状,惟有移来洋人语言,与现代口语结合,渐渐改良,庶几可以让古老的书写柳暗花明。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鲁迅洞悉人间的眼力是超常的。他无疑是一个忠实于存在、历史和自我的人。其一生的劳作,继承了古中国几近消失的文化之光,又把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因素引入到新文学里。他不是建立一个固定的秩序,而是建立了确立自我而又不断否定自我的开放的艺术空间。这个选择避免了对旧话语的复归,也避免了自我的封闭的单向价值判断。一个鲜活的智慧之流在现代史上开始涌动了,我们终于在他的文本里,看到了我们汉语言表达的潜能。(孙郁)